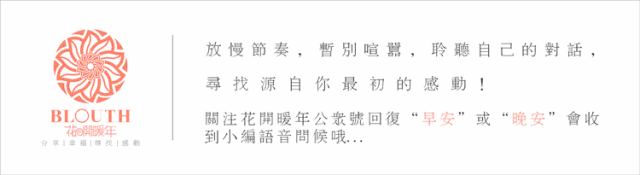
🚀作者:贺依曼 花开暖年 2014-06-05 22:10:29
光线最美的时候是下午四点以后,我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表,四点二十,火车恰好经过黄河大桥。水面缠绵连系着天尽头,坐在下铺靠窗的位置,匆匆往外瞟去一眼,霎时心头一震。水光粼粼,像裹了一层橙黄的,即将融化的糖浆,由近至远皱起叠叠的浅波。但来不及多看一眼,这场景已迅速掠过,很快,连夕阳也悠悠地坠了下去。今年仿佛特别冷。南方的宿舍里湿气极重,夜晚被子多裹上两条,又搭了棉衣,也还是不见暖和。每天上着网,把自己包成臃肿的粽子,手上仍然生出硕大的冻疮。也就是在这比往年显得格外难熬的深冬,因为冷,我竟然萌生了想要提前回家的念头。我从不是个恋家的人,说起来也很奇怪。好像自从三岁开始住校以后,一个人出门在外变得再平常不过,虽然和父母团聚也很值得高兴,但从未因此觉得回家是一件时刻挂在心里且急需完成的事。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地方,早些前我并不愿意回来。不仅外省人谈论起会轻微皱眉,本地人也觉得这城市常年脏而乱,污垢横生,河流阻塞,居民纷扰聒噪,甚至很容易半年得不到雨水眷顾。我爸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感慨,"如果咱们家条件再好一点,我和你妈必然会把你送出去,不管去哪儿,至少让你在十五六岁的时候,能够吸到更干净畅快一点的空气。"而我总说不要紧,以后我总会离开这儿,总要离开这儿的。当时只是期望能看一眼哪怕微微泛蓝的天,见识一下河流到底怎么个清澈明净,而从没有想过其他更为复杂的事。当然更不会知道很多年后才明白的事实——城市里根本没有所谓的蓝天。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愿望甚至更为可怕,幼童对一座城市的抵触就像一根刺,常年深扎在逐渐成长的内心世界里,只有在期许不断实现的过程里逐渐松动。今年夏天我妈突然告诉我,四处辗转后我的户口已落在长沙,这时我猛然惊觉,等了这么多年之后,我竟然真的有一日变成了一个和家乡毫无关联的人。心里那根长刺仿佛终于抖落了出来。在南方绵绵细雨里,空气不再干燥多尘,我却似乎没有感到多少喜悦,只觉得好像隐约间有另一根刺扎了进来。车站里人流如潮。这节车厢里的乘客,大部分和我有同样的目的地,他们无不用家乡方言在我耳边交谈着。一年年过去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静静听着他们的对话一时竟觉得陌生。对话中频繁出现只有本地人才了解是什么的字眼,甚至听见有两个中年男人在讲,我家附近那块算得上偏僻的地价竟然在半年内翻涨了一倍,也开始盖原本没有的高层居民楼。我晃神听着,心中发沉,有些微的酸楚,又深切觉得有些可怕。可怕的无非是这些变迁。而最为酸楚的变迁是什么,我又说不大上来。想起回家后的第一顿饭,饭桌上我妈像抱怨似的跟我提到,XX家的女儿婚后这才第一年,春节七天夫妇俩就跑到马尔代夫玩,不回娘家啦。我说噢?你担心我以后也变成这样?她立马辩解道,这倒不是,以后我是不会管你的,你们年轻人自由安排生活也是对的,我们当妈的不会要死要活拴牢你。我安慰她说,你放心,我以后嫁了人,每年过年也一定会回来。她一听急忙摇手,大声说,我可不是这个意思,可不是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是啥呢,你不回来我们反而轻松。接着跟我爸使了个眼色,我跟你爸商量过了,过两年你春节不在这里的时候,我正好也不用再费心力擀皮儿包饺子了,是吧?我含混的点点头,想笑她故意说这些话给我听,却又不大笑得出来,只得一直扒拉碗里的饭。只听她还在断断续续地讲,市面上速冻饺子这么多,你不知道,我现在年纪大了,连活个面都开始觉得累啦…其实我不是不知道,他们有多想频繁的见到我。前些年在电话里,我妈还会埋怨我为什么总不回我爸给我发的那些短信,我爸在家忧郁的和我妈诉苦,却也不敢当面问我一问。那时我总觉得离家后一下子变得新鲜开阔的生活中,一定有更多比回家更值得眷恋的事。后来随着年纪增长,我逐渐能够明白他们几番委婉透露给我的讯息,但碍于性格中别扭的部分,始终不愿用直接的方式表达感情,从而无法令他们心上得到一些安慰。我总念念不忘的是,这么多年他们尽管如此希望把我留在身边,却何时都摆出一副一定要送我出远门的姿态,并极力让我和他们生活了五十年的城市摆脱干系。而至于这城市,到底有多值得他们这样仇视?今年回来,特意转了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。大多还是保留着原貌,没有太多变化。当年他们送我上学时走过的街道,大抵还是那个样子,路边贩卖零食的种类也没有多出多少。我甚至还能轻易回想起十年前的事,那时候路面要窄一些,巷子再密集一些。记得早晨上学总会经过一间老旧的电冰箱厂,正值上班时间人流从四处涌入一道矮窄的门,我坐在二八车的前杠上,一边指挥我爸笨拙的在人群中穿梭,一边不停拨着车把上那只需要频繁灌油的铃,使它像呼吸不畅的人拼了命从喉咙中挤出一些声响。整个穿越人群的过程中,我记得自己总在傻兮兮的笑,却又不记得是因为什么。这次还特地拐去看了这间厂子,倒是没有被拆掉,那扇从前一到八点准时关闭,下午五点半又准时打开的铁门,竟然还孤零零敞在那个丁字路口。唯一的变化不过是,几年中吝啬的厂长曾命人把它整修得更气派了一些。记得年后初二的清早,他们叫我一道去串门。我找出各种理由推脱。印象里家里人口多,但向来相处寡淡。平时从不见面的三姑四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吃饭,彼此口齿沉重,好不容易艰难开口,问的也是去年已经得到回答的问题。何况我心里很明白,像我这种家族里从不稀缺的低辈分的女孩儿,出现在这种家宴中不仅总被人喊错名字,其实连去与不去也不会有人重视。争执了一会儿,我爸知道拗不过我,唉了一声便走了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,四处望了一会儿,忽然发现这么多年来从不觉得宽敞的房子,寂静下来也实在有些可怕。一瞬间我竟不太能明白,像我妈那样总不甘寂寞的人,是如何在这间房子里熬过了一年又一年。这些年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算短,她耗在这间房子上的时间,和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得一样久了,而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间,可能比我人生中剩下的时光还要长。不知何时开始觉得,这个城市异常缓慢的发展成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。那些令人心头起皱的变迁,好像只有在这些饱含回忆的场景中,才显得不那么飞速。后来每次回来我都变得热爱散步,成长起来的这块地方虽然只有零星点大,却每条街巷都塞满了往日的画面。好像随便走一走,路过一处公园,两滩湖水,看见几个老人躬身打着大个儿的陀螺,脑子里零散的片段就得以拼凑重合。这么多年,在这个城市里即便亲情已经寡淡,朋友只剩零星,但好像依然留存着一些能够让人欣然回返的气息。我没问过我妈对这个她呆了四十年的地方到底存不存在眷恋,毕竟她的童年不在这儿,她的根不在。我不知道,她是否也是在十四岁离开家以后,才明白到另一种至为珍贵的感情,才发觉生活中最可怕的无非是变迁。而最酸楚的变迁呢,不过是以前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所熟悉的一切,那个称之为家的存在,终于有一日改名为——故乡。
